胡适在某个地方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他忘记补充一句:无论怎样打扮,那面容看上去总是不够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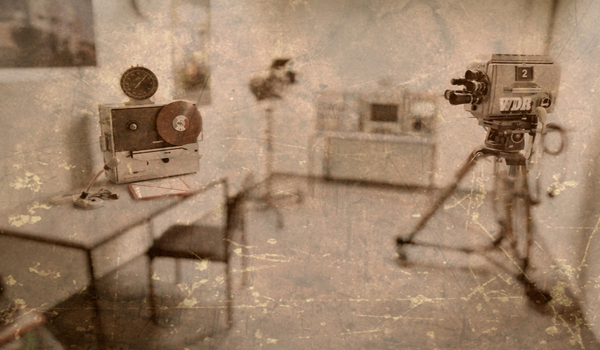
对历史的妆扮,并非虚构与编造,而是将业已发生的事情按照某种线索性因素编排起来,形成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并通过对历史过程的叙述,强化线索性因素的正确性。靠着线索的作用,历史被建构成这样或那样历史主题下的运动轨迹,所有历史叙述都围绕着主题而展开,这就是所谓“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本身和化妆术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以实际存在为依据,通过某种手法突出其要突出的部分,淡化与妆扮目标不一致的存在,以求创造出一个整体协调的全貌。显然,妆扮过后的面貌,与最初的真实存在并非同一事物,二者之间的差距,就是“善”、“美”与“真”的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宏大叙事是对历史的刻意扭曲,它只是试图从纷繁多变的历史事实中寻找一以贯之的主题,把某段历史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同时,在一定的篇幅内对一段历史做概述,也必须要做内容的剪裁,这种剪裁也只能以叙述主题相关的内容为重点,使其在历史上的特殊意义越发突出。
在宏大叙事展开时,近代史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一页。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半个多世纪,中国近代史的叙事结构、时代主题与历史走向,都曾备受关注。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史学危机”以来,宏大叙事日趋式微,而代之以个案研究。在今日,这一问题不但在专业领域处于失语状态,在公共史学领域也被各类趣闻轶事所遮蔽。
为何会走到这一步?如果只强调旧有叙事方式的缺陷,只不过是重弹“史学危机”的老调,若没有对先前各种叙事结构的理性分析,恐怕很难从泥沼中抽身。
从方法论上,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者有着高度的自觉。无论是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还是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从研究取向、学理与学术实践以及叙事结构与叙事手法上,部分回答了中国史历史叙事的困境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反思确实不及这些美国学者那样深入并全面。不过,美国华人学者李怀印——他曾有中国大陆的学术背景——新近出版的《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对近代史的叙事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他的著作专门讨论了中国近代史写作中宏大叙事的形成与形成动因,以及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叙事目的的转变,和主叙事(与“宏大叙事”同义)衰颓时代如何重建叙事结构。
李怀印认为,“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作为中国近代史叙事的两种主要取向,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前者认为中国近代史就是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历程,二十年代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建立民族国家的举动能够推动现代化的实现;后者则认为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在外有列强欺凌、内有王朝压迫的环境下,革命成为时代主题,一次次的革命不断涤荡着旧时代的基础,而这一阶段的历史更应以共产革命的胜利作为终结。
因为对近代历史的最终方向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叙述历史过程时,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各自选取最能体现其叙事主题的事件作为历史的关键点。比如,现代化叙事会选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三民主义”作为重点描述对象,除了义和团运动作为反面例证外,其他几个被描述对象都是被充分肯定的。与之相对应,革命叙事则会选择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作为正面描述对象,强调这些运动的抗争色彩与革命性,而对洋务运动持否定态度。
正如《重构近代中国》指出的,在1949年之后的“十七年史学”中,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革命叙事经过历史学专业内的修正,已经成为中国大陆近代史叙事的大宗;之后的十年左右时间里,因受到政治的左右,并非出自学术表述的、非理性的对革命的强调,扰乱了已经成型的近代史表述。因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近代史叙事既要清除非学术性的历史叙述,也要对“现代化”的时代主题有所反馈。学者们受到欧美学术界研究取向与研究方法的影响,通过对个例的分析,对既有的叙事模式进行颠覆,使近代史从整体变成碎片,这就是近代史叙事的现状。
作为后现代史学批判的对象,“宏大叙事”被认为是一种主观建构,且被视为“合谋”的一部分。正如我用化妆术所做的类比,历史叙事本身并不是对全部事实的再现,而是在某种观念下对历史线索的梳理,和依据线索对历史本身的重新编排,其本意不在于制造历史或篡改历史,而是突出某种观念的力量。展现全部历史事实,无益于我们了解过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未曾记述单纯的文化与经济活动,正是此理。呈现混乱的历史现场,除了让我们感受到当时的活力之外,恐怕我们能够体会的,只有喧嚣与骚动。我们需要宏大叙事,特别是作为与现实联系密切的近代,需要被反思。被解释,被叙述。
近代并不单纯是当代的昨天,也是古代的明天,任何近代史书写者都不可能只谈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历史,他们审视近代的参照系不可能只有当下,还应包括古代。当下作为思考某段历史的出发点存在,但古代作为思考近代的前提存在,过多地强调现实对近代史叙事的影响,而忽视建构近代史过程中对古代史的思考,可以说是《重构近代中国》的遗憾所在。
另有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是,无论是现代化叙事还是革命叙事,都被视为“线性历史”,受到后现代史家的质疑。所谓线性历史,就是从一点到另一点,有明确轨迹的发展过程。在结果已经被知晓的情况下,很容易将此前的历史按照这一结果编排起来,造成一个线性的发展序列。
线性的历史描述会剔除很多偶然性因素,也会对很多对历史结果不造成影响的事件采取忽略的态度,比如近代史叙事中,可能徐悲鸿个人绘画风格的转变就不会作为重要的环节被考察,蒋介石在某一天的日记里表现的个人情绪也不会被看做历史发展的关键因素。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当代的很多史家非常强调这些历史细节的意义,并以书信、日记、档案等材料为依托,展开他们的研究,对原有的线性历史叙述进行冲击。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生动鲜活的细节考察,很多时候是在线性叙述的框架下展开的,如果线性结构的历史主叙事是坐标系的话,他们的研究就是在确定某一个坐标点的位置,或者其位移过程。一个又一个坐标点的发现和确认,有时会对坐标系的绘制提出修正,但不能取代坐标系,更无法取消坐标系。
在专业领域,作为历史坐标系的宏大叙事不可缺席,在公共史学领域,它也同样重要。趣味性的历史阅读是消费行为,而非完整的认知行为。坐标系的重新确立,对于“述往事,思来者”的意义不言而喻。重建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坐标系,总容易让人忧虑,学者和公众都认为重建近代史叙事会与曾经烜赫一时的革命叙事相冲突,事实未必如此。在李怀印的分析中,现代化叙事在二十世纪末遮蔽或者说代替了革命叙事,而从线性的近代史叙事来看,革命叙事未必是不正确的。只要不将其作为近代史的终结点,就有可能重构完整而立体的近代图景。
如果说,过去的近代史叙事有一种“淡扫蛾眉朝至尊”的霸气,未来的近代史叙事,因其对历史和学术的敬畏,应该有点“画眉深浅入时无”的羞怯吧。

